
文|張茵惠(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
IG上出現了一支台灣聲援巴勒斯坦的短影片,畫面中,這位年輕聲援者披著巴勒斯坦圍巾(Keffiyeh),宣稱:「台灣如果要支持台獨,就必須支持巴勒斯坦的自由。」與此同時,《苦勞網》也有一篇文章指教大家「在今日台灣,如何當個左派?」。甚至,這些挺巴人士之中,竟有人聲稱台灣「愧對巴勒斯坦」,並不自量力地將台灣納入「全球軍工複合體」之中。
自2024年以來,台灣部分團體在以哈衝突升溫後舉辦了多場聲援巴勒斯坦的集會與遊行,然而這些行動不僅從名字「從河到海」本身就極度欠缺國際常識,許多與之呼應的網路言論,還粗糙到簡直可以當砂紙拋亮家具。
這波「挺巴行動」不僅暴露了在國際人道議題中,台灣內部長期存在的意識形態撕裂與價值混淆,更完美展現了哲學家布蘭登・沃姆克與賈斯汀・托西在2020年提出「道德誇耀」(Moral Grandstanding)所要警告的惡性範例。
網路討論空間,本質上是一個無形的「地位市場」。在這個市場裡,「道德純潔感」變成了一種可以快速累積社會資本的表現手法。於是,在社群媒體環境下,諸如「挺巴勒斯坦」這類道德訴求不再純粹是為了追求真理或改善世界,而是成為一種自我品牌經營的手段,並且變成了比賽「誰挺得更極端」的選秀節目,而這些道德表演者,無論最初動機為何,最終莫不親痛仇快,掉進中國替「左統」準備好的劇本中。
巴勒斯坦:138個國家承認 vs. 台灣(ROC):12個國家承認
文章一開始提到的那位女性,我想,在採購圍巾之前,她應該先整理的顯非外表儀容,而是自己的邏輯。
若真以「被孤立的民族有資格要求國際聲援」為出發點,台灣的處境遠比巴勒斯坦更加孤立與脆弱。巴勒斯坦至少獲得超過130個聯合國會員國的承認,並自2012年起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而台灣自1971年因受到ROC連累而被逐出聯合國以來,至今在聯合國體系中毫無正式地位,更長期遭中國打壓於國際場域之外。
截至2025年,地球上有138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但台灣受困於「ROC」之名,導致正式邦交國只剩下12國。聯合國觀察員資格,巴勒斯坦有,台灣沒有。國際刑事法院(ICC)接受巴勒斯坦申請案件受理,台灣連申請的「門檻」都無。
倘若這些台灣挺巴勒斯坦人士的道德訴求是普遍適用的,他們理當也必須要求巴勒斯坦方面承擔對台灣的道德責任,並同樣譴責中國對台灣的壓迫與孤立。
但現實是,他們往往選擇性沉默,甚至利用我們的孤立來進行道德勒索,說出諸如「台灣如果要支持台獨,就必須支持巴勒斯坦的自由」、或者「台派們乾脆還給蔣介石公道」、「左派很累,不如當國族右翼簡單」,這暴露出他們所謂「道德聲援」的雙重標準——聲援與否,並非依據普世正義,而是依照意識形態與政治利益選邊,為了讓自己看起來站在道德高地,不妨無視事實任意 PUA 台灣人。
買防彈背心的人,不能只因穿上背心而被指責參與了武器販賣
此外,部分聲稱「挺巴勒斯坦」的人士,將台灣描述為「軍工複合體的一環」,真是我今年看到最好笑的笑話之一。按照他們的邏輯,彷彿只要涉及武器,就與壓迫者站在同一邊。這種說法刻意混淆了正當防衛與軍事侵略的本質差異。
麥可‧沃爾澤(Michael Walzer)的「正義戰爭論」,明確的區分了「防衛性軍備」與「侵略性軍備」的不同。台灣若從防衛自身的角度「參與」武器產業供應鏈,那也與主動侵略、中國在新疆的種族清洗,是完全不同層次的行為。
台灣目前的軍備體系以「自衛性質」為主,且多數武器系統(如飛彈、防空、戰機)是從美國、歐洲等國購買,本身並不是國際軍火市場上的出口國。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數據,台灣在全球武器出口排行中名列極後,主要角色是「進口國」,且購買目的以防禦中國軍事威脅為主。
即使台灣自製少量武器,如自製飛彈、國艦國造計畫,也僅供自衛使用,沒有大規模對外輸出。因此,把台灣說成「軍工複合體加害者」,不僅毫無事實根據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理論基礎,就其本質是「責怪受害者」,並且輕巧把「加害者」──也就是中國──隱身於幕後。
用一句簡單的比喻來說,「買防彈背心的人,不能因為自己穿防彈背心,就被指責參與了武器販賣。」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想當個像樣的左派當然很困難不是嗎?
「從河到海」就是約旦河版的「留島不留人」
「從河到海,巴勒斯坦自由」是當代國際政治中最具爭議的口號之一,台灣脈絡下的運用揭示了政治符號學的基本認知顯然不是人人都有。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於2024年10月開始,以「從河到海,反抗同在」為主題,表達對巴勒斯坦自決與反壓迫運動的支持。
從河到海,指的是「從約旦河到地中海」整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放在哈瑪斯的脈絡中,這句話的意涵就是:「整塊土地都應該屬於巴勒斯坦,徹底抹除以色列國的存在。」在哈瑪斯憲章、和過去的宣傳中,「從河到海」明確帶有種族滅絕意味,是呼籲以色列國家、以色列人民從這片土地上被驅逐、被消滅的暗示。
從歷史脈絡看,這個口號的演變軌跡極具張力。當哈瑪斯在2017年將其納入憲章,而利庫德黨在1977年主張「大海與約旦河之間只能存在以色列主權」時,雙方實際上都採用了地理決定論的排他性話語。這種歷史對稱性提出了關鍵問題:若我們批判一方的極端主張,是否應同等批判另一方的類似主張?追求和平的以色列前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曾明確指出,雙方都必須放棄「從河到海」的極端訴求,才能實踐基於1967年界線的兩國方案。
台灣挺巴團體對此口號的無條件接納,令人懷疑:究竟是愚蠢,還是雙標?當美國眾議院、英國內政部、奧地利與巴伐利亞等將此口號認定為仇恨言論或恐怖主義標誌時,這不僅是政治判斷,更反映了對「模糊滅族意涵語言」的道德警覺。對於正面臨中國「留島不留人」威脅的台灣民眾而言,採納具有類似邏輯的口號不僅在道德上自相矛盾,更可能削弱對本土威脅的抵抗合法性。
對台灣社會而言,審視「從河到海」口號不僅是對遙遠衝突的評估,更是對我們如何理解自身處境的反思。若我們拒絕接受「留島不留人」的滅族邏輯,我們同樣應質疑任何可能包含類似邏輯的國際口號,無論其政治光譜為何。唯有在這種一致性框架下,我們才能構建真正基於普世價值的國際連帶,而非淪為意識形態篩選的代理戰場──正如台灣部分挺巴人士喜歡指控「美國操縱了台灣」,他們卻甘心落入中國敘事框架,這又是為什麼呢?
道德表演:台灣挺巴運動的隱藏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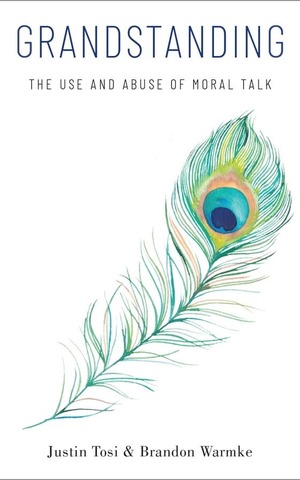
中國經常常針對民主世界的自由派、左派受眾,以人權議題為糖衣,實則引導「敵人打敵人」,進行所謂「逆向殖民」(reverse colonization)──即由極權國家倒過來指責民主國家的人權瑕疵,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中國大外宣近十幾年來刻意推播巴勒斯坦議題,目的是用以取代西藏議題,操作成檢視左派跟自由派的唯一指標。但這何以能奏效?難道全世界的左派都不帶腦?
這必須回到一開始提到沃姆克與托西指出的問題,當人們發表道德言論的主要動機不是解決實質問題,而是提升自身社會聲望或道德地位時,即構成表演性質居多的「道德誇耀」。對於遙遠議題的「關心」,特別適合拿來表演,因為事實上他們除了嘴砲別人信仰不夠純之外完全不需要真的做什麼。這正能解釋為何部分挺巴人士在此議題上的熱衷參與:他們對台灣自身面臨的生存威脅缺乏同等關注度,卻對遙遠的巴勒斯坦問題表現異常激昂。這種現象不只是單純的雙重標準,而是透過特定國際議題的道德表態來鞏固自身在特定社群中的地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這些團體高舉「從河到海」口號時,他們巧妙地進行了道德表演的核心策略,也就是道德綁架(moral hijacking):任何質疑此口號的人都被貼上「不夠關心巴勒斯坦」的標籤。然而,正如沃姆克與托西所說的,道德表演者往往迴避道德複雜性,選擇性地忽略不便事實——在這個案例中,即是中國對以色列鎮壓技術的全面輸出,以及「從河到海」口號與台灣面臨「留島不留人」威脅之間的明顯矛盾。
更深層的分析顯示,這種道德表演的真正目的是「PUA台灣」——透過強化台灣人的道德愧疚感,間接削弱台灣社會對自身主體性的堅持。當某些挺巴團體宣稱「台灣愧對巴勒斯坦」時,他們不只是表達對巴勒斯坦的同情,更是在建構一種道德敘事:「台灣作為美國盟友必須為全球不公義承擔責任」。這種道德炫耀背後,是對台灣主體性的巧妙消解,而這恰恰與左統立場的終極目標相契合,更讓中國喜聞樂見。
威脅層級倒置:台灣挺巴運動的心理政治學
退萬步言,如果台灣某些民間組織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熱烈關注,同時對台灣自身面臨的生存威脅相對冷淡,不是出於邪惡,也不是出於愚蠢,那比較可能是基於什麼呢?這或許可以用「威脅層級倒置」(Inversion of Threat Hierarchy)的心理現象描述之,這意指當社會群體對客觀上較遠、影響較小的威脅表現出更強烈的道德關注,同時對直接且迫切的自身威脅展現相對漠視時所產生的認知失調。
特別值得深思的是,當這些團體激昂地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行動,卻對中國「留島不留人」的存在性威脅保持策略性沉默,甚至出言譏諷關心中國威脅更甚於巴勒斯坦的正常人時,我們必須質問:是什麼心理機制使這種威脅優先順序的倒置成為可能?社會心理學研究提供了幾個解釋路徑,一是「麻木」,長期面臨的威脅往往經歷「威脅常態化」過程,使其失去情感激發力;二是「逃避」,遠方衝突因其抽象性更易被納入純粹的意識形態敘事,不必面對現實政治的複雜性;三是「裝逼」,對遙遠他者的同情提供了較安全的道德表演舞台,不必承擔實質行動的風險與代價。
這種威脅認知的倒置反映了全球化時代地方政治的弔詭,當地緣政治威脅的日常性使其變成背景噪音,反而是間歇性媒體報導的遠方衝突能引發更強烈但根本不切實際的情感共鳴。南非社會學家史丹利‧柯恩(Stanley Cohen)《否認狀態:知曉暴行與苦難的社會心理》(States of Denial: 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提醒我們,這種選擇性關注往往不是純粹的認知錯誤,而是服務於特定身分政治需求的策略性選擇。
柯恩認為,人們面對巨大的不正義時,常常不是無知,而是用各種方式迂迴否認;這種否認不僅是個人心理現象,更是整個社會文化系統的防衛機制。否認有三種類型:字面否認(二二八「沒有屠殺,只是治安事件」)、解釋性否認(二二八「是民眾自己叛亂在先,政府才被迫出手」)、隱含性否認(「我們知道發生過,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要再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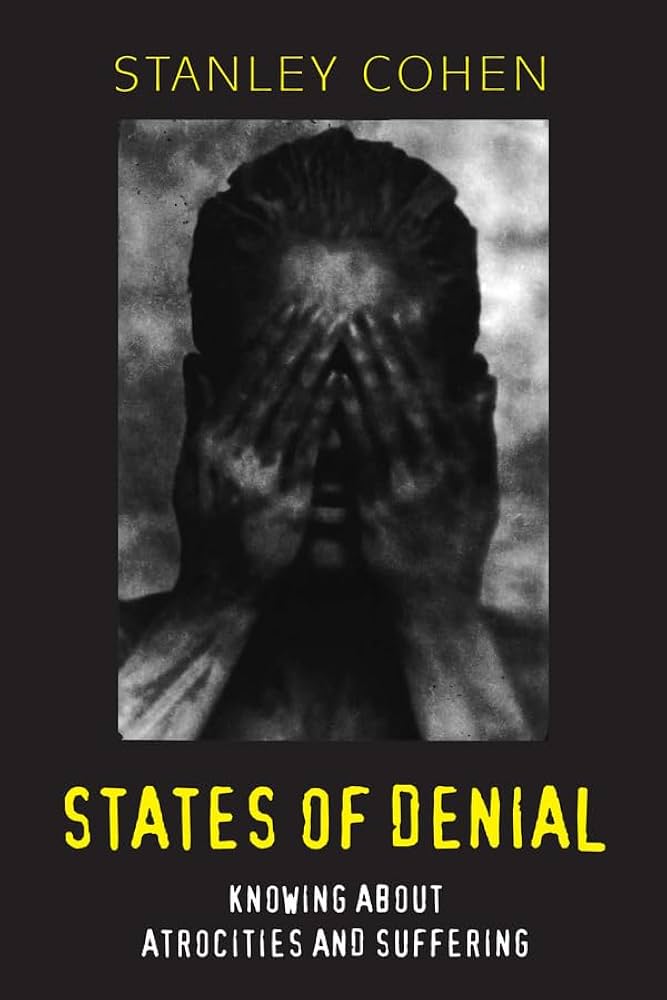
否認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迴避承認事實與責任。在台灣,部分挺巴勒斯坦言論展現出高度的選擇性道德敏感,對以色列的暴行義憤填膺,對中國的人權侵害卻輕描淡寫,難道不讓人聯想到對於台灣真正發生的歷史與當下危機的各種常見否認嗎?
而《否認狀態》一書的英文名字,叫做「States of Denial」,States不只是「狀態」,也是「國家」的意思。台灣是一個否定的國度,台灣人是一個被訓練成「用否定讓自己勉強活下去」的民族。而我們要的,不過是請這些說台灣民族主義很「容易」的挺巴人士,張開眼睛看看,這世界著火了,真的不是只有巴勒斯坦。
我希望那位影片中的年輕人能認識到,「如果支持台灣獨立,就必須支持巴勒斯坦自由」這句話,打從一開始,輕重緩急就是錯的。
問題應該是:「如果支持巴勒斯坦,你怎能迴避台灣的獨立?」
(本文原發表於思想坦克)
書籍資訊
《Grandstanding: The Use and Abuse of Moral Talk》─Justin Tosi, Brandon Warmke,2020
《States of Denial: 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Stanley Cohen,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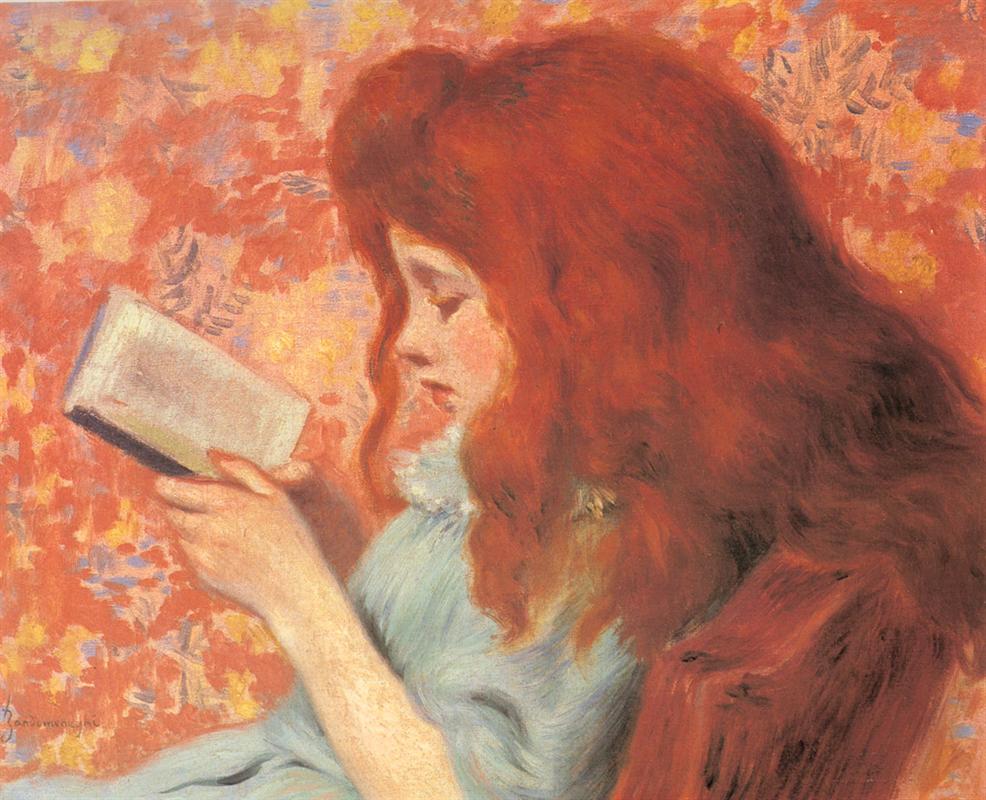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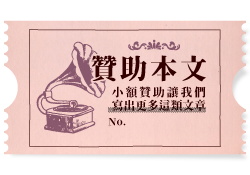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