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為何一度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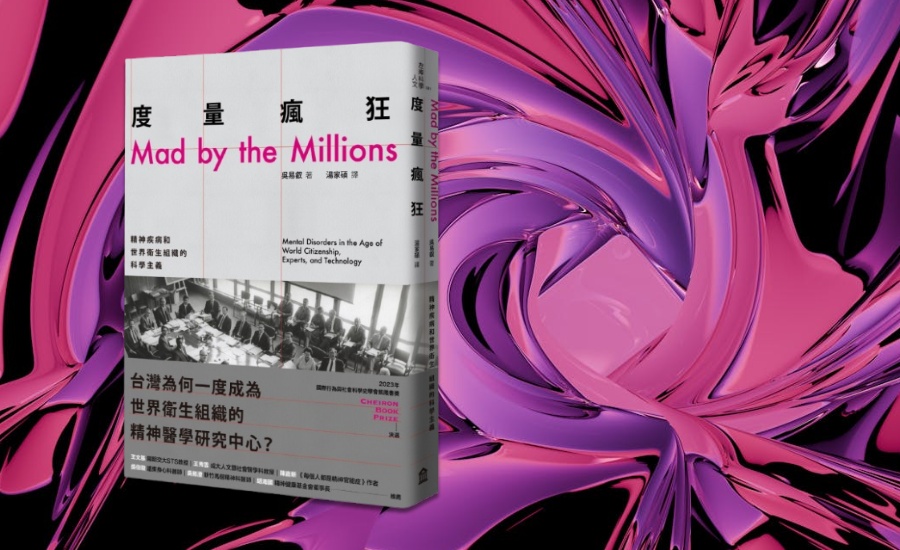
文|吳易叡(Harry Yi-Jui Wu)
譯|湯家碩
「中國」作為科學中的他者
另一個讓林宗義被納入世界衛生組織計畫的因素,是台灣(當時代表中國)精神科醫師與日內瓦主流彼此相呼應的科學立場。自從兩次大戰期間國際聯盟創立以降,來自全球南方的專家(至少在理論上)即被平等視之。二次大戰後,世界衛生組織持續擴大的工作範圍之中,仍包括讓世界各地專家參與的空間,同時間,現代精神醫學要建立其相對於其他醫學專業的學科自主性。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時,台灣的科學家們擁抱了現代醫學的典範,將其科學知識生產活動的價值立基於探求普世的人性和理性,使得專家們自身的民族認同退居次要。這樣的立場讓科學得以在去殖民化過程的戰後台灣持續發展。
然而,台灣精神醫師仍然需要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發展出他們的專業影響力,研究者們因此想要應用他們所接受的日本醫學訓練來進行全國性研究,找出病人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但如同林宗義在其回憶錄中指出,當他進入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任職時,當時所進行的一次調查僅找出了八一九位精神病人。更有甚者,日本精神科醫生在戰後就立即撤離台灣,讓約三百位精神病人頓失照護,只有一位日籍精神醫師負責處理病患移交的工作。在那之後,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取代台北帝國大學成為附設精神醫學部的教學醫院,林宗義則需要面對一個缺乏新政府支持、人員極為有限的精神醫學單位。他二十六歲時,為了要為華人發展精神醫療因此回到故鄉台灣,這樣的企圖反映了他希望達成去殖民化與國家自主的目標。雖然當時的政府官員相當重視殖民醫學典範所帶來的影響,卻尚未體認精神疾病的嚴重性。林宗義和一同草創台大附設醫院神經精神醫學科的同事,憑藉一己之力開辦診療服務。在典藏的病歷檔案中顯示,尋求精神醫學門診幫助的中國移民不斷增加,其中有些人已經有明顯的精神疾病罹病跡象。
林宗義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的動機有很多。他曾經憶及最初是想要研究他的華人同胞的精神疾病樣態。林宗義還小的時候,他曾經對於自己姓名中的「林」究竟是一個日文字,還是一個中文字感到困惑。但成年之後,他因為反對日本殖民,因此自我認同為中國人,他的父親也鼓勵他研究中國人的心理學。除此之外,與戰後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新移民之間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也進一步激發了林宗義的研究取向。他曾經說過,這些中國新移民的心理模式和他預期的有所不同。由於本省與外省人間的衝突,也讓他對族群行為特徵相關的主題抱持濃厚的興趣。
為了調查研究,台灣的精神科醫師進行了非常縝密的資料蒐集。他們不僅採用既有的精神疾病分類標籤,也持續識別出反映文化依存症候群的各種症狀。在研究「台灣的華人」的精神疾病樣態時,林宗義首度觀察到一種罕見的驟發性歇斯底里現象,進一步發現數種在華人族群中盛行的文化依存症候群。其中一種是「邪病」,該症候群的表現特徵是病人會進入抽搐狀態,並且宣稱被死者附身。同時,病人會用怪異的語調說話,內容主要和祖先崇拜有關,持續的時間從半小時到數小時不等。邪病好發於信仰虔誠的人身上,其症狀主包括顫抖、心神喪失、胡言亂語,以及偶發的幻視與幻聽,這與在日本被發現的狐仙附身現象(狐憑き)十分相似。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台灣也發現了與狐仙附身相似的現象,當時主要將其解讀成一種本土的精神官能症,曾經刊載於《台灣醫事雜誌》。這是由東亞的精神醫師發現文化依存症的確切案例。該文作者相信病患發展出的被附身症狀,與內村祐之在愛奴族人身上所觀察到的精神症狀十分類似。其他的範例包括台灣泰雅族的「巫度赫(utox)」現象、愛奴人的「イム(imu)」現象、以及在許多東南亞國家可見的「縮陽(koro)」現象。除了巫度赫之外,林宗義也從其他原住民族身上發現了可被歸類為身心症的症狀,他堅持這些症狀是依存於特定文化而生,而非特定種族。整體來說,林宗義和研究團隊的調查結果,發現精神疾病在各式各樣的人口和族群中所呈現的普世一致性,而他們也因此作出如下結論:文化依存症候群乃奠基於相似的心理學機制,主要是因為壓力和恐懼而觸發。
台灣:一個用於理解「中國人」的實驗場
二戰剛結束,台灣這座島上居住的華人是世界衛生組織方便可及的研究對象。儘管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的面積僅有其百分之○.三七,但當時的中國仍然在共產主義的鐵幕之後。蔣介石控制之下的台灣和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因此都成為學者研究中國的替代品。雖然被以「荒謬」形容,當時被視為「自由中國」的台灣在聯合國著實代表中國的席次。中國是三個提議創立世界衛生組織的聯合國成員國之一,且中華民族佔世界總人口超過五分之一。然而,那個代表中國、成為國際組織想要了解中華文化,以及將全球發展主義應用於中國社會實驗場的地方,竟然是台灣。
台灣在當時是大多數世界衛生組織計畫的實行地,包括護理、親子關係、砂眼等公共衛生介入計畫都曾被導入台灣。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一九五五年開始執行的瘧疾撲滅計畫(MEP)。由於台灣已經經歷某種程度的現代化(尤其是由日本人所建立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且有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援,整個島嶼也在戰後軍事化,因此在一九六五年,瘧疾被成功撲滅。台灣也因此在世界衛生組織招募心理衛生計畫的參與者時,成為全球發展主義脈絡中的要角之一。在心理衛生計畫的主導者討論哪些國家可以被優先選為合作對象時,台灣的排名是第二,僅次於澳洲。當時在世界衛生組織的中國代表是在北京聯合醫院受訓練、後來創立南京腦科醫院的程玉麐。他也曾經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心理衛生小組的專家委員會。但當世界衛生組織的西太平洋區域辦公室從上海搬遷到馬尼拉時,他也移居台灣並在松山錫口療養院執業,曾協助國防醫學院的教學業務。程玉麐最後定居美國,直到退休。
專家們的「夢景」
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顧問系統廣招世界各地賢才到日內瓦,但要讓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精神醫師願意投身一個沒有太多人了解的計畫,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界衛生組織的預算有限,工作環境又特殊,其主要的任務目標在當時也還在雛型階段。在林宗義前往世界衛生組織總部之前,其他專家都紛紛婉拒了它的邀請。舉例來說,伊度亞度.克拉普夫因為家庭因素拒絕了哈格里夫的邀請。就如歷史學家所述,許多國家因為「行政的朝聖」,而在兩次大戰的戰間期將國內的專家派往國際衛生組織。
相反的,世界衛生組織的外包策略則特別側重發展中國家的健康問題,包括中國。世界衛生組織將來自這些國家的專科醫師視為專家,渴望向他們學習,但這些低度開發的國家之所以熱衷於將他們的專科醫師送往世界衛生組織,主要是想藉此獲得更多專業知識與經驗。至於那些在科學相對先進的國家接受訓練的專科醫師,則將他們自己視為與歐洲、日本和北美的專業人員有對等地位。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地科學家的「國族自我形塑」成為重要因素,促使他們在日內瓦彼此合作。這些成為同僚的多國專家不僅可以在國際場合進行溝通,世界衛生組織也是這些國家能在冷戰秩序的脈絡中,用科學和醫學來進行自我表述的絕佳催化劑。大多數的東亞知識份子已經將日本視為國家現代化的標竿。但隨著去殖民化如火如荼的進行,世界衛生組織成為另一個讓他們發展專業素養的平台。因此,林宗義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的熱情,可說是哈佛STS學者希拉.賈薩諾夫(Sheila Jasanoff)和金尙鉉所稱的一種「夢景」。由於林宗義的研究可能存在著統計上的瑕疵,對於性別和年齡所造成的影響也缺乏意識。但他願意移居日內瓦、急切的要說服世界衛生組織:台灣可以對世衛的目標提供重大貢獻。
然而,世界衛生組織心理衛生小組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是一個「交易區」,讓國際計畫中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彼此就遊戲規則達成共識,然後使科學合作成為可能。大多數有將國內專家送往日內瓦的國家彼此之間並沒有聯繫,專家們也各自使用不同的語言且有不同的文化經驗。儘管如此,這些國際合作活動的參與者透過相似的管道抵達世界衛生組織,也都曾接受過類似的現代精神醫學訓練,並且希望能建立全球性的精神疾病比較研究和普世性的診斷準則。若沒有這些志同道合的世界衛生組織參與者與核心職員,心理衛生小組的計畫絕無成功的可能。林宗義在發展中國家,採用嚴謹的流行病學方法進行研究,這是世界衛生組織會優先考慮進行援助的理由,因此獲得許多關注。
一九六四年,林宗義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心理衛生科的醫務官。他隨後起草了包含精神病流行病學共四個子計畫的國際社會精神醫學計畫。該計畫與國際思覺失調症前驅研究(IPSS),後來共同確立了思覺失調症在疾病樣態上的普世性,引導出後來歷史上首次針對思覺失調症進行國際流行病人口學研究、以及史上首次被廣泛認可的精神病分類系統。該計畫需要能分類來自全球大量資料的新統計方法以及電腦運算能力(例如GATEGO軟體)。林宗義對於這些方法並不熟悉,其思覺失調症前驅研究曾經因抽樣和資料校正的方法而受到批評。
更有甚者,思覺失調症只是在UCF第五章的各種精神疾病中有經過流行病學資料驗證的其中一種,其驗證方法後來也被視為存在瑕疵。儘管如此,林宗義和其他在世界衛生組織中的精神科醫師,透過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全球網絡建立了一個專業社群。他們的成就吸引了頂尖的理論家、以及自認為符合世界衛生組織所設計的工作領域的各地專家,他們的投入讓世界衛生組織得以生產和其政策相輔相成的知識。
僅存在於想像中的對等立場
世界衛生組織和其成員國之間的夥伴關係是浮動的,這樣的狀態是因為日內瓦和發展中國家的專家對彼此有著多重想像,然後又進一步強化了國際科學合作。世界衛生組織原本自詡為技術協助的角色,以避免過度引導作為設計原則,目的是譜出一個理想世界。理想狀況下,各成員國的專家無論有多少國際經驗,都有平等機會能彼此溝通、交流、最終會一起執行各種計畫。
然而在現實中,成員國家的去殖民化程度和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差距頗大,日內瓦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態度也因為各國分歧的殖民歷史脈絡而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世衛社社會精神醫學計畫在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一邊是做為該計畫基礎的理念:世界公民身份,另一邊是該計畫在參與國家實質投入心力不均的情形。世界衛生組織對於有些參與國的人才磁吸效應,並無法完全改變當地的精神醫學文化;而做為「黃金標準」的ICD就算經過反覆修改,世界各地在沿用世界衛生組織的精神疾病分類系統時,也還充滿桎梏。
儘管有這些瑕疵,在地與全球層次的科學計畫仍然彼此影響和相互轉化。伴隨戰後科學國際主義的氛圍、由聯合國所提倡和體制化的新國際秩序,新的研究方法也逐漸浮現。科學的共同願景催生出精神醫師之間的合作,這樣的共同願景成為一種平台,能促進國際科學的發展。儘管來自不同國家,由世界衛生組織所召集的專家仍然呈現了相當程度的同質性。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文化背景,而是因為其所接受的訓練類似。這些專家的知識系譜要不是沿襲自各種流行病學思想學派,就是源於與跨文化研究團隊的合作經驗。這樣在智識上的相似性讓他們得以有效率地進行溝通,但這也讓他們失去在世界衛生組織所身處的多元世界中,以不同方式看待疾病的機會。
冷戰期間,各種問題延續著,但世界衛生組織仍然積極蒐集資料,藉以對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進行最佳化。林宗義這位受惠於世界衛生組織援助、代表中國的台灣人,是集所有可行性於一身的醫務主管。我們可以看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社會精神醫學計畫和參與其中的國家所呈現的歷史交會(historical croisée)。這樣的交會主要仰賴四種偶然性因素才得以發生。
第一,儘管承諾要達成去殖民化,該計畫仍然使用了可以上溯至殖民時期的觀念、方法、以及調查結果。第二,在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台灣的科學家建立了能研究華人以及其他族群精神疾病的科學立場。第三,中國在冷戰中維持了數十年的封閉,台灣做為一個距離中國東南處百里遠的小島,對想要理解中國社會的科學家來說,成為一個絕佳的實驗室。第四,包括林宗義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精神醫師,在戰後的新世界秩序中奮力找尋一個能在國際組織的架構中展現他們現代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的夢景」。
林宗義在國際社會精神醫學計畫還在執行的過程中,就於一九六九年半途辭職。但他所留下的工作仍然不間斷進行著。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主義者們繼續追尋各種曾經由林宗義協助建制化的國際科學模式。當聯合國大會在一九七三年投票表決要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擁有中國的官方代表權時,世界衛生組織持續支持在台灣的社會精神醫學研究。這裡,科學超克了政治,雖然只是曇花一現。林宗義在台灣被當作「精神醫學的先驅者」廣為頌揚,但他的許多學生開創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其中,有些人追求更為強調疾病和心理症狀在地脈絡的文化精神醫學,並且和阿根廷的精神科醫師一樣發展出有別於國家官方立場的論述。
然而,在一九七○年間,同床異夢的「全球」與「在地」科學家開始發展出迥然不同的研究取徑。德裔克羅埃西亞籍的精神科醫師諾曼.薩托里斯繼任林宗義,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心理衛生課的領導者。他因推廣社會精神醫學計畫和疾病分類計畫而廣受讚譽。薩托里斯的職業生涯與其他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十分相似。雖然他在共產社會的南斯拉夫接受教育(該國在戰後早期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也經驗到戰火的蹂躪,後來在倫敦毛德茲里醫院接受進一步的精神醫學訓練。然而,當時,世界衛生組的運作模式已經邁入成熟階段,無論領導人是誰,都能十分穩定的運行並有著近似的結構與意識形態。但也因此,後來組織中所發展出的計畫都較缺乏創新。這樣的變遷或許解釋了為何當代全球心理衛生運動是由世界衛生組織之外的思想家所發起。
(本文為《度量瘋狂:精神疾病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主義》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度量瘋狂:精神疾病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主義》 Mad by the Millions: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Age of World Citizenship, Experts, and Technology
作者:吳易叡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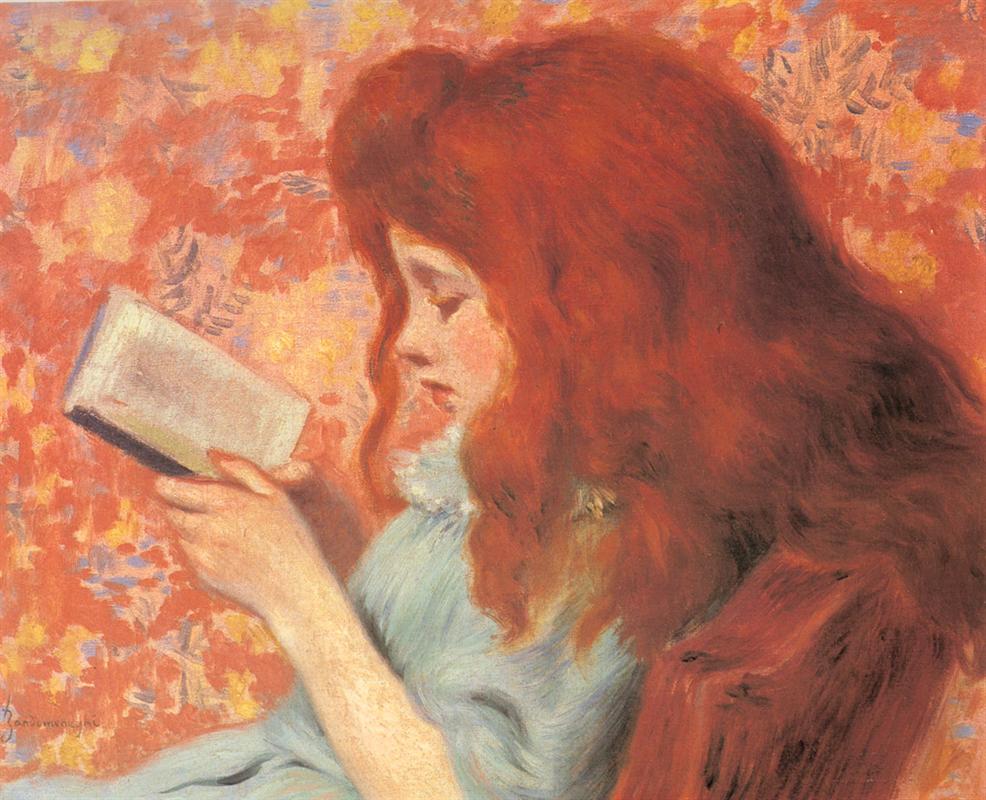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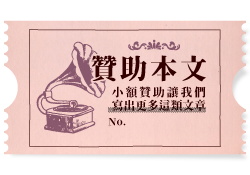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