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Karen Hitchcock(澳洲執業醫師,文學作家)
譯|劉思潔
政商名流就是我們的宗教信仰,是我們的人生導師,教導我們穿什麼、買什麼、要有什麼模樣,現在還教我們該怎麼思考。他們領導各種人權和動物權的倡議運動,也為了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中的嬰兒大聲疾呼。現在甚至有政商名流為安樂死背書支持。看起來,安德魯.丹頓(Andrew Denton)儼然變成專家了,因為他做了八個月的研究──比取得技職學院的伺酒師文憑所需的時間還短。八個月,他一再強調,彷彿這格外超凡,就好像我國在這項爭議上,並沒有一大群正反雙方的支持者──他們都投入數十年認真思考關於安樂死的各種複雜議題。
我曾跟他一起上過一個電視節目,他在後台對我說,會進行一次「友善的討論」。「我非常緊張。」他這樣跟我說,而我當時緊張得口乾舌燥、手掌冒汗;他還很客氣地加上一句:「我覺得妳寫的文章好看得不得了。」節目一開始,丹頓就宣稱醫師是該開始聽見病人的聲音了,並且多次打岔、反駁、打斷觀眾的問題,他的語氣極度屈尊俯就,令我這個資歷尚淺的醫師當場被修理一頓。我心想:我們都不准對安樂死提出任何質疑嗎?這變成一種信仰了嗎?
丹頓說,我們是該討論死亡了。「是時候了。」他兩眼直視著攝影機,擺出總理把複雜議題簡化為口號的模樣。看起來,將安樂死合法化,就能夠進行這種討論。事實上,這種對話已經展開,儘管多半是在討論會進行,沒那麼大張旗鼓。
安樂死造就了非常棒的電視節目收視成績。我們都聽過某些人被痛苦折磨的揪心故事,於是非常想要找到方法來幫助人脫離悲慘不幸。不過,死亡是唯一的解決方法嗎?認為應該賦予這些顯然充耳不聞的醫師──就算不是笨到極點──殺人的許可,這不是有點怪嗎?
「安樂死」這個字眼就是指殺人的行為,「醫師協助自殺」也是。語言對於形塑思想有很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名實相符、實話實說。如果我開立處方,病人服用這項藥物時,我就有責任,這就是行醫的條件,否則所有的藥品就都可以自行臨櫃購買了。加州很可能會重啟死刑,因為發現有些單一藥物能確保達成「人道又有尊嚴的死亡」──連死刑這麼恐怖的事情,也可以重新塑造成一種給予尊嚴的行為。提倡安樂死的人運用強大卻圓滑的措詞:「協助自殺」被宣傳成一種「控制」自己的死亡和保障「尊嚴」的方法。這個爭論已經落入避重就輕的美言,殺人的權利被重新塑造成死亡的權利。國家賦予醫師的權利,被重新塑造成擴展平民百姓的權利。有人批評我使用「殺人」的講法,而假若殺人的行為如此令人不快,我們就應停止主張讓醫師做這種事。
在我們的文化裡,死亡既是無所不在又是隱匿不見。小孩子上高中之前,就在螢幕上目睹無數的殘暴死亡畫面,卻往往不曾近距離看見老年人離世。對於人類身體的死亡,我們有一種消毒過的期望。自然死亡可能猝然發生──手摸胸膛、表情驚恐、然後倒下來──或是緩慢發生:九十五歲的老人漸漸不吃不喝,身體器官進入寂靜。強迫全家人守在床邊好幾天,看著摯愛的家人昏迷不醒、「挨餓脫水至死」,到底有什麼意義?並沒有明顯的意義。但是,殺死失去意識的瀕死者,只是減輕家人的痛苦。瀕臨死亡的人既不餓也不渴,雖然胸腔嘎嘎作響,他們其實是睡著的,既不會記得也不會回憶起這最後兩三天的事,因為他們快要不在了。
的確,由於缺乏安寧緩和照護服務、臨床工作人員所受的教育不足,病人可能會承受原本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因為臨床醫護人員不敢給病人「太多」嗎啡以免「被控殺人」,而造成病人瀕死時承受著無法控制的疼痛,那麼就有需要釐清涉及雙重效應原則的法規:有時候,控制臨終症狀所需要的藥物劑量,也會導致加速死亡。這個原則被丹頓等人拒斥為「緩慢安樂死」,卻是根據一道簡明的律令,也就是醫學的基礎:醫師處理病症而非處理生命。生命永遠不會是疾病,死亡也絕對不會是療法。
很多駭人聽聞的故事,都是由於哀痛不已的家人沒有預備好面對摯愛之人的去世,在這段期間又溝通不良,事後也沒有接受喪親的哀傷輔導。他們只擁有善終或歹死的記憶,而他們的記憶則取決於他們對事件的詮釋、對屈辱的定義、醫院的慣例,以及他們與逝者的關係。這些都是很複雜的議題,無法以乾脆一死來解決。
我在大型公立醫院擔任醫師十二年,照顧過好幾百位垂死的病人,當中沒有哪個人臨死時大吼大叫或央求我殺了他。當病人說自己很想死時,我對此的反應是:「請告訴我,原因是什麼。」很少是因為疼痛,通常是由於絕望、寂寞、哀傷、覺得沒價值、無意義或變成累贅。我從來沒見過哪個垂死的病人身體上的疼痛是無法處理的。嗎啡加上密達唑侖(Midazolam)效果極為強大,可以非常快速地給藥且滴定到最佳藥量。巴必妥類藥物(Barbiturates)可以在幾分鐘內讓人失去意識。安寧緩和照護的做法,在過去十年當中已有長足的進展。
有很多研究都顯示,末期病患對於加速死亡的渴望,主要是來自絕望的感受。我們必須傾聽並試著處理這種感受及其他的恐懼。知道自己快死了,會是很痛苦的事:對於不存在感到恐懼。大力鼓吹安樂死的團體中,有數以千計高學歷的富裕成員,對他們而言,要能奮力掌控人生中唯一無法完全支配的部分,寧眠他(Nembutal)這種安樂死藥物是唯一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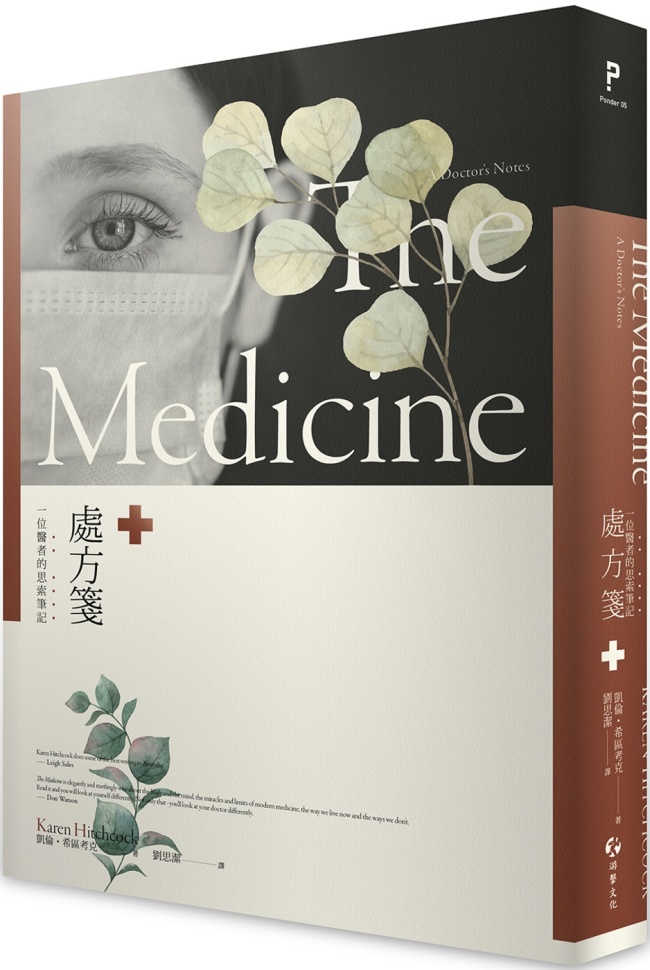
將人類主體簡化地理解為完全自主的個體,是基於一種意識型態,那很吻合現今的另一種主流意識型態:自由市場。在現今的世界裡,兩種意識型態主要都是對優勢者有利。
當我們被視為只不過是自由市場上的自由行動者,需要照顧和協助就變成羞恥的事,照顧人的行為則被視為一種付出,而不是一種相互增益的經驗。我們把一些人安置在養護之家,那個地方加速他們的認知和身體衰退──保留他們的白內障、省去牙齒和助聽器、把他們固定在電視機前面然後圍著抹布當圍兜、若非絕對必要就避免碰觸他們。然後我們覺得他們面目可憎。我們一想到需要協助或照顧就不寒而慄,這對於那些有需要的人造成極重大的影響。我們所說的是「你們死掉還比較好」,而沒有全體一起努力改善他們的命運。我一直覺得驚訝,西方國家的改革派政黨竟然最大力提倡安樂死。我以為改革派政見的基礎,是深信許多個人「權利」(持有武器、燃用石化能源、拿到全數薪資)可以為了社會整體的好處而適度妥協。在死亡的議題上,我們卻忽然好像只是一堆人恰巧位於同一塊土地上。
如果死亡變成面對虛弱無力時的一個選項,那麼虛弱無力就會被變成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生活方式的選擇是個人的責任,我們的社會責任消失了。
我國雖然擁有龐大的集體財富,卻經常聽到醫療及福利制度無法永續的呼籲:資源嚴重限量供應,安寧緩和照護及相關臨床教育的資金短缺。老年人和殘障者的照護只得到小氣又吝嗇的配額,因為人民只是經濟單位,被區分為是否具有個別生產力。
我們可以尊重自主權和自由意志的神聖性,但人的決定會受到環境、同儕團體及社會期望的影響。形式上的同意並不保證是自由選擇的決定。更重要的是,病人的決定會隨著時間而有變動;然而,一旦死去,就無法改變主意了。
什麼是「無法忍受的痛苦」?社會整體應該如何回應這樣的痛苦?如果我們不再設法幫助覺得人生太苦而想退場的人,而是協助他們結束生命,這對醫療的核心工作來說意味著什麼?在比利時,死亡現在是憂鬱症「無法治癒」時的一種合法治療。有人說這樣很勇敢。你需要的是第二意見!就好像在面對國家認可的殺戮時,還有某種防護措施。沒多久以前,腦葉切斷術曾是首選的治療方式,你也需要這方面的第二意見。醫師可能跟任何人一樣瘋狂、不智、犯錯、被誤導。我們要怎樣把人分成該協助自殺和該避免自殺這兩類呢?在奧勒崗州,只有六%的精神科醫師說他們可以很有信心地斷定,某種精神疾病不會導致病人要求結束生命。應該由這六%的醫師來做決定嗎?不必等多久,醫療保險公司就會把他們收集成一份名單了。
預期壽命是很難預測的,而且「痛苦」這種說法涵蓋了非常多的感受和情緒。痛苦的程度總是主觀的。人類具有一種獨特的能力,會在功能受限又虛弱的生活中找到意義,甚至能樂在其中──尤其是免費得到照顧的時候。慢性疼痛的診間擠滿了沒有末期病症的病人,他們經驗著自己覺得無法忍受的疼痛,但往往並非器官的病症,而是處在心理—社會混亂的情況下。這些人該得到一死嗎?或是我們應該繼續提供心理和社會的支持,並且研究神經可塑性的方法,幫他們找到平靜?假使我們決定以死亡作為治療,又何必多此一舉?
有些人主張要把「存在的痛苦」──為了活下去而付出的一部分代價──視為死亡的一個徵兆。存在的痛苦,是大部分的人在某個時間點都會感受到的,大多數罹患重病的人更是如此,而這可以是智慧的來源。
拒絕治療是一種權利,要求醫療照護也是權利。自殺並不違法,雖然我們盡力預防有人這樣做。殺人或要求被殺,都不是道德或法律的權利。安樂死是用便宜行事的解決方法,來處理棘手又複雜的照護問題:照護那些依賴者、受苦者、垂死者。我們搜尋一條清楚的界線,超過這條線時就該同意:對,你的生命不值得活了。這條界線向來很武斷,而且那是個峭壁懸崖,而非一條界線。
試圖讓死亡變得輕而易舉,無可避免地會令社會上很容易提前死亡的弱勢者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是個累贅。沒有任何醫師專門小組或法規小冊、制衡原則,能夠預防這種基於新式社會規範而產生的無形脅迫。最前線的臨床醫師會看到這個無形脅迫的作用:病人因佔用床位而道歉、因身為累贅而道歉、因覺得自己惹人厭而道歉,於是希望自己可以一死。
我可以理解為何殺生會被塑造成一種對於機能衰退、身體折磨及心理痛苦的人道反應。但我們身為醫師,有責任幫忙把你的生活變得可以忍受。我期盼這個社會能有允許我們這樣說的價值觀和資源:「別怕,我們會照顧你,幫你減輕疼痛,見證你的痛苦。不會的,我們不會殺死你。」
(本文為《處方箋:一位醫者的思索筆記》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處方箋:一位醫者的思索筆記》 The Medicine: A Doctor’s Notes
作者:凱倫‧希區考克(Karen Hitchcock)
出版:游擊文化
日期:2021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