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一些人來說,「歐姬芙」這個姓代表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對另一些人來說,「歐姬芙」這個姓,指向不止一位藝術家。
2014年,喬治亞‧歐姬芙的《曼陀羅/白色花朵一號》拍出了4,440萬美元的價格,打破了女藝術家作品的拍賣紀錄,讓她成了「世界上最貴的女藝術家」。喬治亞也是第一個在MoMA舉辦回顧展的女藝術家。但她並不是家族裡唯一一個畫家。
艾達.歐姬芙是喬治亞‧歐姬芙的妹妹,家中的第三個孩子。藝術是艾達的畢生追求,她在輾轉不同的兼職維持生計時,仍然堅持繪畫,留下了許多作品,但是她的名氣卻遠遠不如姊姊喬治亞.歐姬芙。

喬治亞.歐姬芙幾乎從不畫人,她對自然界更感興趣。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喬治亞只畫「自己」──她的內心對世間萬物的感受、投射和再創造。
無論繪畫花朵、沙漠還是河流,喬治亞都知道如何簡化它們,簡化成最基本的線條和色塊,保留它們最本質的內核。喬治亞能把人們以為自己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暴露出一種嶄新的美——寂靜的、壯闊的、永恆的美,在她的作品裡,小到動物骨頭,大到沙漠,都有這種美。
喬治亞突破了歐洲傳統繪畫的等級框架。只要看一眼她畫的風景和靜物,你就很難再想像,有什麼人類的形體能比她呈現的那片曠野更神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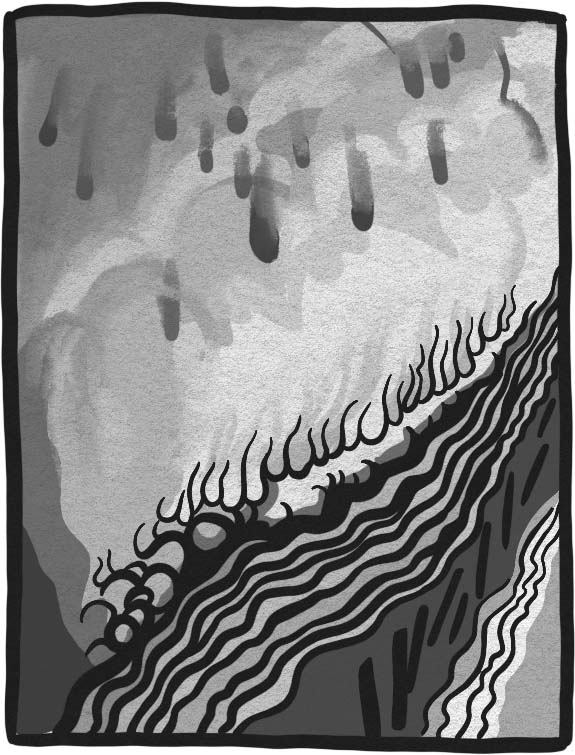
艾達.歐姬芙嘗試從描繪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出發,創造一種精確的平衡感,呈現一種嚴謹的、按部就班的美。我們生活的世界可能看起來亂糟糟的,實際上卻依照某種嚴謹的內在規律在運行,而艾達的畫就展示了這種奇妙的秩序感──人造的燈塔、海面上的光線、浮動的船隻都可以被均勻地切割、變形、重新鋪排,直到嚴絲合縫地融合在一起。
艾達.歐姬芙在繪畫中刪除了意外和動盪,可惜,這些意外和動盪在人的生活中是刪除不掉的。

喬治亞喜歡收藏一切
喬治亞與兄弟姊妹在農場長大,土地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食物、靈感和證明自己的方式都從土地裡來。喬治亞是長女,在七十多歲時,她還能在散步時順便用手杖打滿滿一盒的響尾蛇,給採訪她的攝影師看。
喬治亞是個收藏家,響尾蛇不過是她的收藏品裡微不足道的一種。她收藏花朵、石頭,外出時能撿到的各種紀念品。她還收藏巨大的東西,比如天上的星星。有一天夜裡,最小的妹妹克勞迪婭與喬治亞在德州的曠野裡散步,四周除了地平線什麼也沒有,勞迪婭把瓶子扔到天上再用槍打下來,而喬治亞忙於看星星,後來她畫了許多水彩畫。喬治亞能用抽象的色塊重現那個夜晚滿天星星給人的感覺,讓那些星星最終屬於她。
在那個時候,喬治亞的父親已經賣掉了農場,母親得了結核病,家一貧如洗,但喬治亞的收藏總是很「富裕」。喬治亞奔波在各州靠教美術勉強糊口,也總會在閒暇時繪畫,收集記憶、情緒、頭痛欲裂的感覺。1916年的一天,她的朋友把那些畫拿給著名的攝影師斯蒂格利茨看,讓斯蒂格利茨大為傾倒,斯蒂格利茨就是喬治亞未來的丈夫。
艾達的生活總是被打斷
和艾達比起來,喬治亞絕對算不上活潑。艾達身上有用不完的精力,熱衷跳舞、騎馬,是學校裡的合唱團和籃球隊成員,她外出回來時總會帶一束漂亮的花,並且把它們插得像一幅畫一樣好看。艾達總是能在日常生活裡找到樂趣。對畫畫的喜歡,戰爭和貧窮都不能阻擋。
艾達最喜歡的還是畫畫,不過她只能斷斷續續地學習。在戰爭中,許多人的生活都是這樣,隨時可能被打斷,而機會也許就在夾縫中出現。
一戰期間,艾達受訓成了一名護士。1925年,她在當一個有錢人的私人看護時開始自學油畫。在當時的美國藝術界,如果想要被人當成一個嚴肅的藝術家,你就要畫油畫,像那些歐洲大師一樣。艾達從身邊的美妙事物著手,比如畫瓶子裡的花、桌上的蘋果或是海灘上的遊客,進步神速。1927年,喬治亞邀請她參加畫展,《紐約時報》對「艾達.登.艾克」的畫讚譽有加。那時,喬治亞早已在紐約聲名大噪,卻沒人發現艾達也是歐姬芙家族的一員。艾達用了從去世的媽媽那裡繼承來的中間名字作為姓,也許是希望避開姊姊的陰影,即使這片陰影終將覆蓋她。

「不管我畫什麼畫,他們都覺得是女性內在欲望的表達」
1918年,丈夫說服喬治亞搬到紐約,正式向美國藝術界介紹她,而她不用多長時間就得到了紐約人的喜愛,這可能是因為,她總能提供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讓人發現那些習以為常的事物被遺忘的細節,或是讓人看到他們從未留心過的事物。
喬治亞最讓人瘋狂迷戀的就是她那些奇異的花朵繪畫,畫的像是被放大了無數倍的花的內部,那些柔和的顏色,細膩的質地,一層一層包裹起來的寂靜的世界,擁有某種神祕的吸引力——沒人見過那麼迷人的花朵。喬治亞不是依照生物學的標準描繪花的結構,而是用顏色重現她看一朵花時的感覺。給一朵花足夠的時間,讓它充滿你的眼睛,你會因此發現,花朵竟然可以如此壯觀。
姐夫把喬治亞的畫當作一種女性內在欲望的表達(就像超現實主義者們習慣思考的那樣),這一觀點影響了不少評論家。連花朵也可以那樣解讀──因為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所以它應該是人類欲望的比喻。對一些人來說,花朵總是沒有人類重要。喬治亞對這類評論很厭煩,為此,她將不惜放棄自己最擅長的題材。
發明一種永恆的燈塔
在第一次展覽成功後,艾達趁熱打鐵,申請了哥倫比亞大學下屬的應用藝術學校,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學習,並最終在那裡拿到了藝術學學士和碩士學位。

在那段時間裡,艾達對燈塔特別著迷,開始嘗試創作抽象繪畫。在那一系列作品裡,燈塔射出的光線變成線條、色塊和形狀,成為景物的一部分,讓人彷彿看到一座永恆的燈塔,持續轉動,照耀它身邊的事物,而它發出的每一種光都得到了忠實的記錄。這些變幻的光線和它周圍的景物,都依照艾達計算好的動態對稱構圖方式鋪排,和燈塔這個形象本身的比喻相得益彰──它永遠穩定,引領人走向一個理想的世界。
1933年,這些畫在紐約展出時,艾達使用了自己的真名。評論家熱切地表達了對它們的好奇,卻用了一種「危險」的方式──他們說,「歐姬芙」不再只是一個人的姓,而是代表了一個藝術之家。也就是說,從那時開始,艾達正式成了大藝術家喬治亞.歐姬芙的妹妹。
發明一種永恆的曠野
1929年,喬治亞到新墨西哥州旅行,並在那裡改變了美國現代繪畫的面貌。
那裡沒有喬治亞習慣畫的那種花,僅有一望無際的沙漠、連綿不斷的紅色山丘,以及難以計數的動物骸骨。而喬治亞把這裡所有的沙漠、山丘、雲朵、天空和骸骨都重新「發明」了一遍,讓雲朵變成柔和的抽象符號,山丘變成連綿不斷的色塊,骨頭則變得異常巨大,無聲地漂浮在沙漠之上。她的畫面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氣質,如果從未被工業打擾,自然理應就是這樣的,哪怕是再微小的骨頭,也是壓倒性的、撲面而來的、壯觀的。從來沒有人這樣描繪曠野。後來,藝術史學者說喬治亞.歐姬芙是「美國現代主義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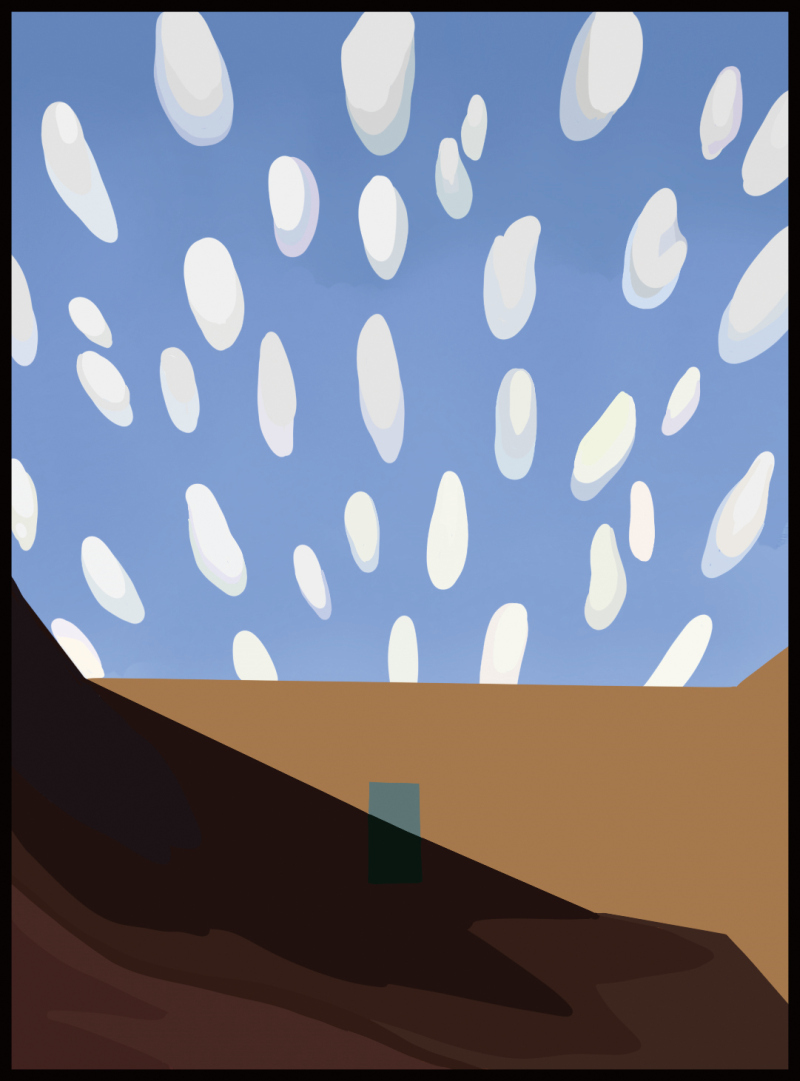
我想,喬治亞更喜歡的稱呼是「旅行者」。丈夫去世以後,她常常到國際旅行,把更多風景畫到畫布上,比如從飛機上看到的雲朵、縮小成幾條線的河道、古城遺址的巨大石牆。我想,如果地球繼續轉動,而喬治亞還能繼續畫畫,她就不會停止拾撿生活當中奇妙的事物。
烏鴉的遊戲
當艾達忙於在畫布上構建一個秩序井然的世界時,美國大蕭條開始了。
接下來的十幾年中,艾達藉由不同的兼職維持生計,教書、寫短篇小說、做護士、畫壁畫,總是為了臨時工作搬家,連個固定的畫室都沒有。一旦有機會,艾達都會參加展覽,爭取更多的曝光,但是人們總把她當成「歐姬芙的妹妹」。除了畫燈塔,艾達一直沒有機會停下來鑽研其他主題,發展出一個穩定的風格,更沒有遇到一個堅定的支持者。
1943年,艾達搬到加州隱居,再也不外出展覽,最終在那裡去世。克勞迪婭保留了艾達所有的畫。
艾達曾經為小學生畫科普書,介紹印第安人文化。那本書裡有一篇故事叫《烏鴉的遊戲》,描繪了一個保護玉米田不被烏鴉啄食的小孩。小孩說,有些烏鴉朝玉米衝過去,人就會追,這時候,另一些烏鴉就會在樹上呱呱叫,這就是烏鴉的遊戲。也許,人生有時候也是這樣,為了各種各樣的原因奔忙,煞費苦心,最後其實只像一場遊戲。
藝術史只能記住一個人
在生前的時候,喬治亞.歐姬芙就已經成了時代的偶像。
喬治亞是20世紀被拍攝得最多的藝術家之一,擁有無數的追隨者,人們認真研究她的家居裝潢、飲食習慣和生活哲學。
1938年,《生活》雜誌說喬治亞是「當下美國最著名的女藝術家」,並刊登了她身穿黑衣在沙漠中拾撿頭骨的照片。
人們仰慕的喬治亞就是那樣的形象:獨自一人,在美國西部沙漠跋涉的冒險者;創造了真正獨特的視覺符號的藝術家;一個生活中永遠不缺乏奇妙細節的女人。
有趣的是,艾達也是這樣的人。艾達也是個冒險家,走過美國的許多地方,尋找解構日常生活景物的方法。如果有人感興趣的話,艾達在插花方面的創造,或者對騎馬的熱愛,應該也很值得研究。甚至連兩人的妹妹凱薩琳也曾經說:「喬治亞和艾達並不合得來,因為她倆太像了。」
但是,藝術史最終只能留名一個人。在兩個相似的歐姬芙之中,藝術史只需要一個歐姬芙。
於是,一個擁有紀念碑,另一個擁有藉口。

喬治亞‧歐姬芙:
「藝術史最後留下了我。不過,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偶然。在我活著的時候,我就在考慮怎麼編輯我的歷史,控制我畫作的價格,決定哪些畫能賣出,哪些畫值得留在博物館。我反覆訴說我的故事,直到所有人都覺得我的版本才是真相,他們只能看到我願意展現出來的部分。」
艾達‧歐姬芙:
「藝術史最後忽略了我。不過,我不覺得那是決定性的失敗。未來的日子還很長,我的許多畫現在還沒有被找到,等你們看到它們的時候,一定會大吃一驚。」
|在克勞迪婭死後,艾達的作品散失了,有的甚至出現在跳蚤市場上。至今,艾達的許多畫仍下落不明。|
(本文改寫自《漫畫.圖解「被消失」的藝術史》)

書籍資訊
書名:《漫畫.圖解「被消失」的藝術史:花朵、毛毛蟲和疼痛也能成為創作主題!23位女藝術家挑戰時代與風格限制,讓藝術的面貌更豐富完整》
作者:李君棠
繪者:垂垂
出版:漫遊者文化
日期:2023
[TAAZE] [博客來]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