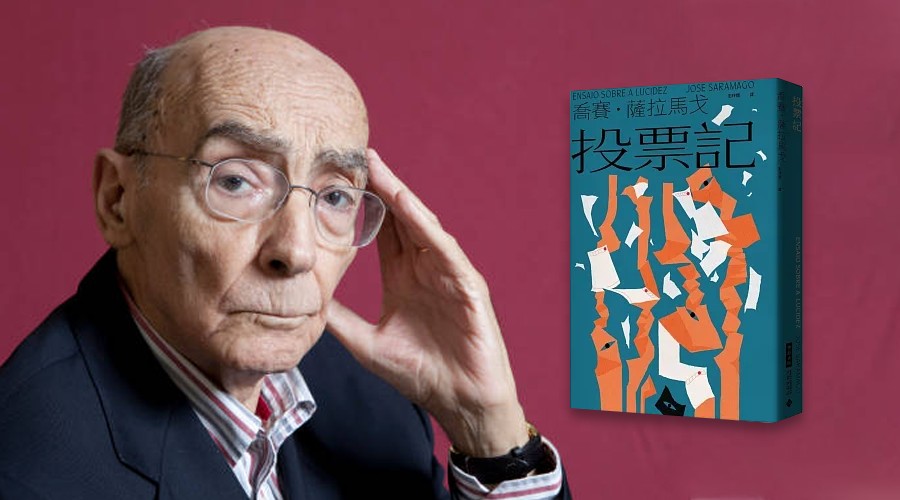
一個有趣的問題:投一張空白票算是犯罪嗎?
在自由和平等掛帥的民主社會中,沒有明文條款反對這件事情,也沒看過任何一個國家對此祭出法律重責(除非這個國家原本就沒有票可以投)。它或許會被譴責沒有行使應然的公民權利,但人民擁有選票,本來就可以自由決定要選出哪一位公僕,所投出的票也和票匭中另一張平等:在此前提之下,你甘願忍受麻煩冒著大雨,在投票日當天打著傘,拿了身分證到投票所領票,只為了在最後投下一張空白票嗎?一個人或許還好,可以理解他不想要濫竽充數、都沒有喜歡的候選人,或者純粹就是心情不好,想做一次微小的反社會報復,但當整個區域有超過83%的人都投下了空白票,探討核心就不只是犯罪,而是人們最常說卻又輪廓模糊的詞彙:政治。
從盲目到清醒的過程
閱讀喬賽.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作品好比倒吃甘蔗,起初會因為連串、毫不停歇的寫作口吻而感到吃力,但當習慣了這種手法,便會對書頁中所述的情節以至於概念著迷不已。還記得陪阿瑋去燙頭髮,我坐在一旁看《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絲毫不覺得三、四個小時就這樣流逝,也驚訝於經典竟能同時保有可讀娛樂性和深邃概念。作為續集,《投票記》(Ensaio sobre a lucidez)的原文書名是「關於清晰的散文」,恰好與前作「關於失明的散文」形成對比。盲目的象徵很明顯,但民主與清晰的關聯卻顯得諷刺──怎麼樣才算是看得見,這不僅僅是生理上視網膜的映現,更關乎心理人們決定要看見什麼。
《盲目》敘述人們遭逢一種怪疾,會如疾病那般將眼前全白的失明狀況傳染給下一個人,整個族群於是陷入了返祖的社會結構,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從中有猜忌、掠奪和殘暴,但同時也能見到毫無怨言的犧牲。奇妙的是,這疾病並未無止境地蔓延,某天突然便毫無來由的痊癒,如它毫無理由的出現。四年之後,同樣地點舉辦選舉,如上述所言,大雨後的投票所開出70%的空白票,當局大為震驚,對於選票結果不信任,馬上發表聲明,數日後舉辦第二次選舉,結果天氣晴朗的第二次投票,空白票不降反升,來到83%,總理這次不只是震驚,更是震怒,直言選民破壞了民主價值的底蘊,開始試圖懲罰那些投下空白票的人民。
白成了一句髒話,人們用牛奶色來代替那個不能說出口的形容詞,當誰問你投什麼票是必得要緘默。情治單位分析大量群眾言談的語句,卻無法分析出什麼確鑿鐵證,「我想這事總有一天 會發生的吧」,爪牙聽到破碎片語,試圖想讓它成為呈堂供證,「那樣的話,你不覺得比較自然的反應是嘆氣嗎」,當權者要將千萬群眾的反應套入單一模板,雞蛋裡撈骨頭,眼神裡網出謊言,人民若不符合政府的設想中的應然面貌,那便有鬼,成了上層要抓的倒楣鬼。
※您可能也想看:我的恐懼是一片光亮──薩拉馬戈《盲目》
超越現實的美好公民
特別的是,薩拉馬戈並未從底層角度去敘寫人民被刺探的苦楚,反而故事前段都圍繞在各種長官之間遊轉,宛若隱形鏡頭紀錄下他們會談中的各種轉圜:總理、國防部長、內政部長、文化部長……沒有名字,只有科層化頭銜彼此斡旋,他們焦頭爛額地想抓出事情原委,這麼大的事件不可能是巧合,絕對有什麼組織在背後運作云云。在荒謬到略顯幽默的討論之中,我們目睹到很罕見的一件事:這次似乎是群眾占了上風,猶如每次湯姆貓都抓不到的那隻傑利鼠,臉上都映著慧黠的笑,嘻嘻。
眾所皆知,群眾沒有面孔,數十萬心緒所編織出的集合體難以測量,沒有理論可以精準判斷群眾下一步會往哪裡走,但薩拉馬戈筆下這群投出空白票的群體卻完美到不真實:他們懂得用各種機巧語言搪塞、用測謊機反將情治人員一軍,彼此之間也絲毫不見各種對立衝突,甚至在政府決定封城徹逃的深夜,整座首都點亮了高官們即將駛離的道路,提燈、檯燈、聚光燈、手電筒、銅製油燈,「指出了道路,照亮了背棄者的逃生路線,好讓他們不致迷路,也不致走岔了路」。這個魔幻場景過份美好,也近乎明顯地把明亮的象徵搬上檯面,理想公民們用一種明亮且和平的方式,指向顢頇政府在黑暗中應該走離的道路。
或可把這超乎現實的公民群體作為薩拉馬戈的政治理型。身為共黨成員,他並不相信真正的民主能夠實現,表層說和平轉移政權、以群眾為主,但政權之間無可避免會有數以千計的黑市交換,階級利益會在檯面下角力,意識形態也可能左右籌碼,到最後,民主僅是裝腔作勢的一場秀,選票是散場時舞台飄下的廉價雪花。所以他假想了一個精明、溫和(封城時沒有任何暴力舉措)、沉穩(就連內政部長放下炸彈後的遊行也都毫無戾氣)到不可思議的群眾,一個現實世界或許再不可得的群眾狀態,去反襯,或者說一種希冀,公民與執政者可以不必上下交相賊,甚至公民可以站在比較高的台階上,替槍管插上一枝康乃馨。
「......向他說明投空白票的人之所以投空白票,並不是為了搞垮制度奪取權力,因為就算奪了權力,他們也不知道要拿權力來做什麼,這些人之所以投空白票,是因為他們的希望幻滅了,且找不出其他方法來清楚表達這幻滅是有多麼深沉……」(頁95)
敘述裡只能見到各種職稱,不見個人名姓,常有人說這是體系的詛咒,告訴你只要在換了個位置就會換了腦袋,升上當老闆絕對會變得黑心,選上高官必然會剝削下層,那麼當人從這些頭銜中解脫,賦歸回沒有權力的千萬面孔時,遺失的腦袋會不會重新接回來?他會不會重新想起來(甚至有些愚笨),覺得權力這東西到底可以拿來幹嘛?的確,利益交換之下的選票是最沒價值的一張廢紙,因為你沒辦法選出有價值的那個人選,選擇不落印章,反倒成了通往民主價值最近的途徑。
空白票雖然是廢票,但它實際上一點也不廢。
大於政治的人
如果前半部分還像是一場荒唐的黑色幽默電影,《投票記》的後半則是逼近人內在本核的偵探懸疑劇碼。在經歷連串風波後,政府高層收到信件,指出四年前有位醫生的妻子並未陷入盲目疾病,暗示她必然和空白票動員有所牽連,於是內政部長派出了三位警員負責調查四年前醫生妻子所照顧的一群人,試圖找出那本來就不存在的證據。
黨只需有個標靶,開槍之後再畫上個圈也算是射中目標,但當中的荒謬讓負責的大隊長愈發不安,任誰都知道這只是欲加之罪。書中並未實際探入大隊長的內心,去仔細描摹他的心緒轉折,但讀者可以從他日常舉措的各種遲疑,找到那善良的輪廓。尤其喜歡有段情節,大隊長跟蹤帶著狗散步的醫生妻子,想要告訴她當局已經有所動作,繼上次到她家偵詢過後,這是他們第二次對話。他們來到個公園,醫生妻子對大隊長的警告給予致謝,卻未顯得過份驚慌。她只是安撫那隻對大隊長嚎叫的狗,然後大方邀請對方到家裡來吃個午飯。
「妳確定嗎。確定什麼。確定要讓我坐上妳的餐桌。是的,我確定。妳不怕我會耍妳。看到你眼睛裡的那些淚水,不,我不怕。」
很簡單的場景,卻道盡了醫生妻子面對不實指控的沉穩,以及大隊長在應然與實然間的良心抉擇──相較於書中其他人都只有稱謂、沒有面孔,此時讀者卻可以清楚看見他們的名字,那是出生就能宣讀於口的美好和善良。
政治,是各種團體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然以最寬鬆的定義而論,人在與其他人彼此斡旋、試探、協商裡,也都藏著名為政治的行為。誠然,身在他人生活圈之中,我們很難脫離一系列的算計與被算計,但縱使人生來就被政治包裹著,薩拉馬戈相信,我們內在應該有某些東西是與生俱來,無法被量化、利用或指控的、超出政治兩字能夠囊括的範疇。當醫生妻子最後在電話裡問大隊長,為什麼要如此幫忙時,大隊長是這麼回答的:
「我們出生的那一刻就好像簽訂了某種終生協議,但是有一天我們會自問,是誰替我簽了這紙協議。」
身而為人,我們有太多需要遵守的不成文合約,要孝順父母、要懂得環保、要對感情忠誠、要在周一早上起身上班……有些簽訂在前,有些在後,但大多時候都像個愚騃的客戶,人家叫我簽,我當然就簽了,明明看房貸合約時如此仔細精明,但對於生命本身因循的各種限制和呼籲,人們倒習以為常。當初到底是誰替我簽了協議呢?無神論的薩拉馬戈肯定會說,沒有上帝手把手的引領誰寫下字跡,從頭到尾,身而為人的都只有你自己,唯有意識到這紙需要負責的紙面,才會仔細閱讀上面的詞彙,而不是逕自拉到最下面點同意。
《投票記》從政治角度切入,直指政府高官體系敗絮其中,各種欺瞞推託和踢皮球,但我喜歡的是,在諷諭之外,仍有一點稀微火光,告訴你公民有投空白票的自由、告訴你說,人可以撕破官僚俗世的工作合約,只為了遵守另一張有著更加美好願景的協議。
書籍資訊
書名:《投票記》 Ensaio sobre a lucidez
作者:喬賽‧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
出版:時報出版
日期:2022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